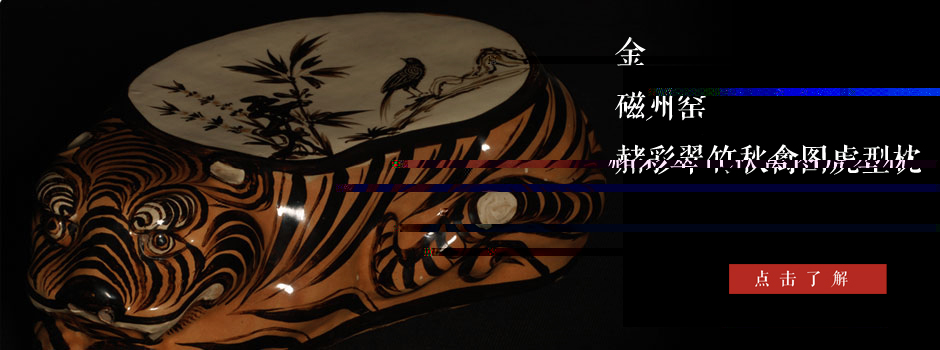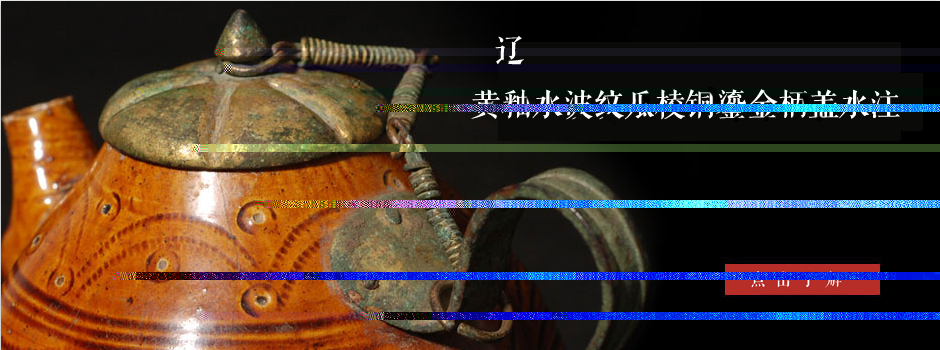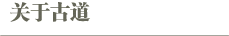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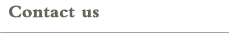
地址:中國北京朝陽區建國門外大街1号國貿寫字樓1座614-616
Tel:+86-10-65051177
Fax:+86-10-65058988
E-mail:soongs@zbkenuo.com
宋人插花物語
瓶花的出現,早在魏晉南北朝,不過那時候多是同佛教藝術聯繫在一起。鮮花插瓶真正興盛發達起來是在宋代。與此前相比,它的一大特點是日常化和大眾化。其間的區別不僅在於規模和範圍的不同,更在於氣象和趣味的不同。而影響欣賞趨向的有一個很重要的物質因素,便是家俱的變化,亦即居室陳設以憑幾和坐席為中心而轉變為以桌椅為中心。高坐具的發展和走向成熟,使精緻的雅趣有了安頓處。瓶花史與傢俱史適逢其時的碰合,使鮮花插瓶順應後者的需要而成為室內陳設的一部分,並與同時發達起來的文房清玩共同構建起居室佈置的新格局。唐宋時代室內格局與陳設的不同,由傳世繪畫和近幾十年發現的墓室壁畫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花瓶成為風雅的重要點綴,完成於有了新格局的宋代士人書房。它多半是用隔斷辟出來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,宋人每以“小室”、“小閣”、“丈室”、“容膝齋”等為稱,可見其小。書房雖小,但一定有書,有書案,書案上面有筆和筆格,有墨和硯,硯滴與鎮尺。又有一具小小的香爐,爐裡焚著香餅或香丸。與這些精雅之具相配的則是花瓶,或是古器,或其式仿古,或銅或瓷,而依照季節分插時令花卉。這是以文人雅趣為旨歸的一套完整的組合。花瓶作為要件之一,已在其中占得固定的位置。
詠及幾案花卉的詩,在宋人作品中可以說俯拾皆是。如曾幾《瓶中梅》:“小窗水冰青琉璃,梅花橫斜三四枝。若非風日不到處,何得色香如許時。神情蕭散林下氣,玉雪清瑩閨中姿。陶泓毛穎果安用,疏影寫出無聲詩。”。又劉辰翁《點絳唇·瓶梅》:“小閣橫窗,倩誰畫得梅梢遠。那回半面。曾向屏間見。風雪空山,懷抱無苟倩。春堪戀。自羞片片。更逐東風轉。”詩雲瓶梅如畫,詞雲它本來是屏風上的寫真,卻又從畫中脫“影”而出。上海朵雲軒藏宋人《寒窗讀易圖》,便恰好是“小閣橫窗”的書房一角[圖一]。書案上的其他陳設均被山石掩住,畫筆不曾省略的隻有書卷和瓶梅,小瓶裡橫枝欹斜,梅英疏淡,宋人的無聲詩與有聲畫原是低回著韻律一緻的梅頌。如果說牡丹是唐人的花,那麼梅可以算作宋人的花,南宋陳景沂輯《全芳備祖》,其“花部”以梅為冠,正是時風使然。張耒說:“個人風味,隻有梅花些子似。”牡丹在唐代很少插在瓶中作為幾案清供,梅花卻如同沉香一樣,長在書室中與宋人的詩思相依傍,由花瓶護持的一縷冷香便總能為各種環境下的生存帶來閒適和清朗。

[圖一]《寒窗讀易網》(局部)止海朵雲軒藏
“花瓶”一詞用來專指插花之瓶,其出現於文獻的時間是在北宋。溫革《瑣碎錄》卷二“雜說”條雲:“冬間花瓶多凍破,以爐灰置瓶底下,則不凍,或用硫磺置瓶內亦得。”溫革是政和五年(1115)進士,《瑣碎錄》最早著錄于陳振孫的《直齋書錄解題》,今有明抄本殘卷存世。同卷中關於鮮花插瓶的各種知識尚有不少,如:“牡丹、芍藥插瓶中,先燒枝斷處令焦,鎔蠟封之,乃以水浸,可數日不萎。蜀葵插瓶中即萎,以百沸湯浸之復蘇,亦燒根。”而與他約略同時的李綱有《志宏見和再次前韻》,句雲“蠟封剪處持送我”,所送者,牡丹也,詩中記事與《瑣碎錄》的說法正是一緻。《瑣碎錄》又雲:“牡丹、芍藥,摘下,燒其柄,先置瓶中,後入水,夜則以水灑地,鋪蘆席,又用水灑之,鋪花於其上,次日再入瓶,如此可留數日”;“蓮花未開者,先將竹針十字卷之,白汁出,然後插瓶中便開。或削針去柄,簪於瓶中”;等等,所記多是經驗的總結,可見當時鮮花插瓶的風氣之盛。南宋釋寶曇《花瓶》詩雲:“轆轤聲中井花滿,亦有口腹如許清。百花叢中度朝夕,一點不關流俗情。”便是借擡眼可見的尋常物事聊寄胸中的一點清奇。
古之所謂“瓶”和“罌”,還有“壺”,適用的範圍很寬泛,水器、食器都可以稱罌,稱瓶,稱壺。罌,《說文·缶部》雲“缶也”:《廣雅·釋器》“罌,瓶也”:《漢書·韓信傳》顏注:“罌缶,謂瓶之大腹小口者。”瓶,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三:“似罌而口小曰瓶。”又《急就篇》卷三顏注:“壺,圓器也,腹大而有頸。”作為生活用器,自名為“瓶”、“罌”者,式樣並不一緻。早期插花之器也或稱罌。兩晉南北朝直到隋唐,各種式樣的長頸瓶已經很流行,插花應是它的用途之一,時當初唐的昭陵長樂公主慕壁畫即有這樣的形象。其慕室甬道東壁的持物侍女圖中,一位上著綠披帛、下著條紋裙的女子手捧鼓腹撇口的長頸瓶,瓶口低低探出一枝蓮蓬和一莖待放的蓮花“[圖二]。這自然是一個很明確的例子。不過瓶花作為居室陳設特別是幾案陳設,宋代以前尚沒有蔚成風氣。風氣的形成實與傢俱變化的推助密切相關,這是前面已經說到的。

[圖二]昭陵長樂公主墓壁畫
宋代花瓶在形象設計上並沒有全新的創造,隻是選擇了造型優美的幾種,使它從古已有之的瓶罌樣式中獨立出來,而予以比較固定的用途。如果作一個大略的區分,那麼可以說設於廳堂的大花瓶,其造型來自糧罌食瓶的成分為多,而設於幾案的小花瓶,式樣多取自上古青銅禮器。見於詩人題詠者,最常見的便是膽瓶、小瓶、小壺、瓷瓶;又古瓶、銅瓶。實物中,有兩組很好的例子,一見於杭州鳳凰山老虎洞窯址,一見於四川遂寧金魚村窖藏。不過前者窯場及出土器物的性質究竟何屬,目前尚在討論中。後者時代約當南宋末年,而包含的品類更為豐富,並且時間跨度很大,是彙聚了很可以體現時代風尚的一批器物,其中花瓶正是重要的一項。
體現著雅趣的花瓶原是隨著桌、案的發達因陳設的需要而興盛發達起來,為與書案上的文房清玩相諧,它自然也以小為宜。陳與義《梅花二首》“小瓶春色一枝斜”,又嚴參《瓶梅》“小瓶雪水無多子,隻笏橫斜一兩枝”,所詠即是。嚴參詩又收在楊萬裡《誠齋集》卷五,題作《昌英知縣叔作歲坐上賦瓶裡梅花時坐上九人七首》,那麼嚴氏白為坐中九人之一。七首之二雲:“膽樣銀瓶玉樣梅,北枝折得未全開。為憐落莫空山裡,喚入詩人幾案來。”若賦筆果然實錄,則坐中插梅之瓶乃是小銀膽瓶,且設在幾案。而所謂“小壺”,也是可近筆床可依書燈的小瓶之類,由前弓l古訓可知,“腹大而有頸”的“圓器”均可稱之為壺,它與瓶並沒有嚴格的區別。窗外竹,室中畫,焚香,插花,對弈,乃是鋪陳風雅的幾項基本設施,正所謂“閣兒雖不大,都無半點俗”。不過於宋人,膽瓶很可能是用來表述花瓶中的一大類,長頸鼓腹而曲線柔和,即其形略如垂膽者,大約便是宋人眼中的膽瓶,所謂“圓壺俄落雄兒膽”,“垂膽新甍出汝窯””,又徐兢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》卷三一“花壺”條“花壺之制,上銳下圓,略如垂膽”,都是大緻相同的描述。
上銳下圓、形若垂膽的花瓶,其實早已見於南北朝藝術中的瓶花圖案。如龍門蓮花洞南壁左側佛傳故事中,悉達多太子身後一個細頸圈足的大花瓶,瓶裡插著蓮花與蓮葉,其時代為北魏後期[圖三]。又山東臨朐北朝畫像石慕出土的一方畫像石,下有覆蓮座的長頸瓶裡插著蓮葉蓮花,與雲氣中的青龍合為一個畫面[圖四]。不過直到宋代,膽瓶之稱才開始叫響,並且成為宋人花事中常見的話題。膽瓶造型優雅,線條簡單卻很俊逸,鼓腹容水,修頸容枝,瓶口小而微侈,正宜捧出花束而又輕輕攏住,因此特為宋人賞愛,它出現在時人畫筆下便總是與花事相連,比如最常見的采花插瓶。故宮博物院藏南宋冊頁《採花圖》,江蘇武進縣村前鄉南宋五號慕出土的戧金仕女遊園圖朱漆奩,都是描繪親切的例子[圖五:1—2]。與畫面中形象相近的實物有不少,如北京地區出土的兩件高近30釐米的瓷瓶,又如四川遂甯窖藏中的龍泉窯小瓶,高15釐米,江蘇宜興和橋宋募出土的褐漆小瓶,高11.9釐米。,雖大小有別,材質不同,造型稍異,但大緻都可以歸入宋人所說的膽瓶之屬[圖六]。

[圖三]龍門蓮花洞雕

[圖四]臨朐北朝畫像石墓出土畫像石
 [圖五:1]《採花圖》(局部) 故宮博物館藏
[圖五:1]《採花圖》(局部) 故宮博物館藏

[圖五:2]戧金仕女遊兩岡朱漆奩(局部)
江蘇武進縣村前鄉南宋墓出土

[圖六]青瓷瓶 北京懷柔縣出土
不過這裡尚有一個問題,即作為酒具的玉壺春瓶,宋金時代,它的式樣與大型膽瓶幾乎相同,而出現在慕室壁畫中,其用途多表現得很清楚,比如河南焦作市北郊老萬莊金代壁畫募中的一幅侍女奉酒圖[圖七]。不妨認為,玉壺春瓶是從膽瓶這一大類中析出的一支,它以用來盛酒而美其名日“玉壺春”,但玉壺春瓶同時也用作插花,圖像所見正是如此,比如前面舉出的南宋戧金仕女遊園圖朱漆奩,而宋詞中早有著這樣的敘事。北宋曹組《臨江仙》有“青瑣窗深紅獸暖,燈前共倒金尊。數枝梅浸玉壺春”,可見玉壺春瓶用來插梅是毫無疑義的。它與膽瓶是同類,由馮子振《梅花百詠》和釋明本的和詩可得一證。馮氏《梅花百詠·浸梅》雲:“旋汲澄泉滿膽瓶,一枝斜插置幽亭。冰姿玉骨清如許,隱隱風聲入座馨。”明本同題和詩雲:“插花貯水養天真,瀟灑風標席上珍。清曉呼童換新汲,隻愁凍合玉壺春。”原唱雲“膽瓶”,和作呼應其意而變換語詞切其事日“玉壺春”,正可見二者原本同屬,因此在時人的觀念中它有這種可以互換的一緻。馮子振與明本生活的時代大抵相同,均是由宋入元。

[圖七]奉酒網焦作市金墓壁畫
花瓶的陳設,在幾案,在廳堂,都有一個重要的要求,即穩定,因此多為它增配器座。李葬《山庵》:“花梨架子定花瓶,一朵紅梅對懺燈。賈島佛前修夜課,臥冰庵主是詩僧。”“花梨架子定花瓶”,幾案陳設也。以定瓷之素雅推送出梅花之清瘦,山庵遂成詩境。花開“一朵”,自是綴於一枝。日本南禪寺藏傳南宋馬公顯《藥山李翺問答圖》,正仿佛為此詩寫照[圖八]。這是宋人筆下的唐人故事,藥山手示上下,曰:“雲在天,水在瓶。”一支畫筆卻繪出宋人鍾愛的膽瓶,膽瓶裡又是宋人鍾愛的“一朵紅梅”。

[圖八]《藥山李翺問答網》(局部)日本南禪寺藏
瓶插一枝,欲求其熨貼,不能不說也是一項藝術,花枝要選得好,品種要合宜,花瓶與花也要韻緻相諧。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南宋《盥手觀花圖》,繪花事爛漫時節的一幅庭院小景,長案上一具長頸瓶,瓶身形若倒扣的敞口杯,修頸兩側各綴一對雙環,小口中聳出鮮花一枝[圖九:1]。項元汴《歷代名瓷圖譜》著錄一件宋龍泉窯器,名作“一枝小餅”,式樣與此圖所繪相同[圖九:2],“一枝小餅”的命名或是出自明人,它也見瓷網譜著錄于張謙德的《瓶花譜》,即所謂“瓷器以各式古壺、膽瓶、尊觚、一枝瓶為書室中妙品”,但其式淵源以及欣賞趣味當追溯到兩宋。

[圖九:1]《盥手觀花網》(局部)
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

[圖九:2]“一枝小錯”《歷代名瓷圖譜》著錄
《盥手觀花圖》圖繪閨閣花事,又著意畫出花器的不同。長案前後各有一個方幾,後面的一個放著口沿裝飾鼓釘紋的花盆,前面一個置花瓶,長身細腰,編紋歷歷,可以認得是竹器,瓶裡一大捧菊花。竹瓶和菊花的相配,仿佛更能留駐花的淡雅。而竹花瓶的佈置得宜也還有另一個很好的例子。《南宋館閣錄》卷二《省舍》一節說到濯纓泉上有木橋,上有竹亭,泉東有竹屋一間,“周回設斑竹簾,中設黑漆棹一,竹花瓶一,香爐一,石墩十二”。看得出,古樸、清雅是竹屋之韻,而黑漆棹上的竹花瓶便是特地安排的點睛之筆。
截竹為筒,筒插鮮花,本來也是宋人花事中的雅趣之一。鄧深《竹莆養梅置窗間》:“竹與梅為友,梅非竹不宜。截莆存老節,折樹凍疏枝。靜牖初安處,清泉滿注時。暗香披拂外,細細覺春吹。”竹筒製作的花瓶自難久存於世,因此不知它曾否流行,不過宋代瓷器中有一種筒形瓶,今人常稱作“花插”,其設計或即從竹筒取意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兩件南宋官窯器,日本根津美術館藏一件屬龍泉窯[圖十:1—2]。筒形花瓶在繪畫中,也有合式的對應。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傳蘇漢臣《妝靚仕女圖》,圖繪對鏡理妝的女子,妝具之側一個小木架,木架裡面正好坐一具插著鮮花的花筒[圖十:3]。而鏡旁陳設花瓶,在宋代並非僅僅是女子的雅尚,士人也常把它視作逸趣且付諸吟詠。樓鑰《以十月桃雜松竹置瓶中照以鏡屏用浦韻》:“中有桃源天地寬,杳然溪照武陵寒。莫言洞府無由入,試向桃花背後看。”方回《開鏡見瓶梅》:“開奩見明鏡,聊以肅吾櫛。旁有一瓶梅,橫斜數枝入。真花在瓶中,鏡中果何物。玩此不能已,悠然若有得。”把對“格物”的偏愛貫注到對生活細節的關注和體驗,使宋詩並不總是詩意豐沛而宋人詩心長在,鏡中瓶梅便是詩心燭照下的一點玄思,“照鏡梅”也因此成為後世詠梅詩中常見的一題。

[圖十:1]南宋官窯花筒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

[圖十:2]龍泉窯花筒 日本根津美術館藏

[圖十:3]《妝靚仕女圖》(局部)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
如前所述,宋人的鮮花插瓶,常常用到的尚有瓷瓶、古瓶、銅瓶。楊萬裡《道旁店》:“路旁野店兩三家,清曉無湯況有茶。道是渠儂不好事,青瓷瓶插紫薇花。”又高翥《靜對》雲:“靜對爐煙一縷霞,謝天成就澹生涯。安排瓦硯臨章草,收拾瓷瓶插鄭花。”前舉小瓶、膽瓶、花筒,其實均以瓷器為多。開篇所引曾幾《瓶中梅》“小窗水冰青琉璃”,插梅的花器自然也是青瓷瓶。此外也還有瓷花瓶而式仿古銅器者。
宋人的尚古,本是源自對古今之別的體認。宋《政和五禮新儀·卷首》錄有大觀年間制定禮儀之際君臣間的一番討論,其中徽宗的意見很耐人尋味,便是“禮緣人情,以義而起,因時之宜,禦今之有,故商因于夏,所損益可知;周因于商,所損益可知,而不相襲也。善法古者,不法其法,法其所以為法之意而已”;而“世異事殊,衣冠器用,其制不同。弁笄組紈、篚篋簟筵,皆古人之常用,其制度非今人之所見,品官之家,豈能遵行。可改用今人器用,制禮具令,將行天下”,總要使今禮“簡而易行”。它的引人注意,即在於有此明確的古今之別,才能夠把所謂的“古”從作為“今”的現實生活中獨立出來,而安放在可以從容涵泳的藝術氛圍中。“古”於是有距離,有魅力,所謂“古鼎”、“古瓶”的古為今用,比如焚香,比如插花,方見出它典雅雍容的魅力。詩詞中的“古瓶”、“古晷洗”、“銅彜”,都是對上古銅器的並不嚴格的泛稱,而同時代的繪畫也常常把這種尚古之情化為具體的形象,如宋徽宗《聽琴圖》(故宮博物院藏),又南宋冊頁《瑤臺步月圖》、《漢宮圖》(臺北故宮博物院藏)等[圖十一至十三]。
 [圖十一]《聽琴網》(局部) 故宮博物院藏
[圖十一]《聽琴網》(局部) 故宮博物院藏
 [圖十二]《瑤臺步月網》(局部) 故宮博物院藏
[圖十二]《瑤臺步月網》(局部) 故宮博物院藏

[圖十三]《漢宮網》(局部)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
審美情趣之外,古銅器的插花,也包含著宋人的養花經驗與知識。趙希鵲《洞天清祿·古鐘鼎彜器辨》:“古銅器入土年久,受土氣深,以之養花,花色鮮明如枝頭,開速而謝遲,或謝則就瓶結實。”銅本是植物生長發育所必須的微量元素之一,它既可作為植物體內參與氧化還原過程的多酚氧化酶的輔基,又可以使植物因銅素營養充足而增強抗寒能力。此外古銅器表面因水和二氧化碳的長期侵蝕而生成的銅綠,乃是鹼性碳酸銅,原有殺蟲、殺菌和防腐之效,銅瓶插花,瓶裡的水因此不易變質,瓶裡的花則可吸收銅離子以為營養。當然“謝則就瓶結實”的可能性是很小的,《洞天清祿》所舉即便是實,也隻是特例。
至於銅瓶,其稱很早就已經出現,不過在北宋以前,所謂“銅瓶”,以指淨瓶,又或汲水之瓶、溫酒之瓶為多。皮日休有詩詠栽植藥草事,句雲“銅餅盡日灌幽花”此則汲水澆花之瓶。宋人說到銅瓶,方才涉及折枝插瓶,便是插花和養花,而以北宋末年直至南宋為盛。所謂“古瓶”、“銅瓶”,南宋時候已經是很常見的商品,因此南宋末年的《百寶總珍集》特從商家角度講述二者之間的區別。其卷六“古銅”條前面四句口訣雲:“古銅元本出周時,舊者花粗入眼稀。丁角句容花兒細,此物應當價例低。”並解說道:“古銅堅者顏色綠,多犯茶色,多是雷紋,花樣皆別,今時稀有。鼎、花瓶、雀盞之屬,丁角、句容及台州亦有新鑄者,深綠色,多是細少回文花兒,不甚直錢。”這裡所說出自新鑄的“花瓶”,便是詩詞所詠養花插花的“銅瓶”。銅瓶的式樣或是最為通行的膽瓶,或四方瓶、八方瓶,如遂寧金魚村窖藏的出土[圖十四]。又或仿古式而作成銅觚,亦即後世所謂的“花觚”、“美人觚”,前舉《瑤臺步月圖》、《漢宮圖》所繪即是。福建南平市區大橋工地出土的一件南宋銅觚,可以說是一個比較標準的樣式[圖十五]。與此同時,瓷花瓶的仿古,古銅禮器之外,也多取銅觚為式。

[圖十四]遂甯窖藏銅瓶高155釐米

[圖十五]銅觚 福建南平市區大橋工地出土
此外尚有一類也是用作插花的大瓶,高多在三四十釐米,或者更高一點。北方遼金募葬磚雕或壁畫中常有它的形象。[圖十六]。有的瓶頸處系彩帛,這原是佛教藝術中的寶瓶式樣,當然大瓶的主要發展線索仍是此前作為生活用具的瓶罌。與作為幾案陳設的小瓶相比,這一類安排在廳堂的大瓶開始流行的時間或稍早一些。以圖像為比照,北方窯址屬於宋代遺存的若幹大瓶應可定名為花瓶,河北磁縣觀台磁州窯址所出即是比較集中的一批。[圖十七]。幾種大瓶造型的淵源也都很早,但用途大約始終比較寬泛,直到宋遼金時代鮮花插瓶作為家居陳設蔚為風氣,才成為大緻固定的花瓶式樣。

[圖十六]河北宣化遼張世卿墓壁畫

[圖十七]觀台磁州窯址山土花瓶 高23.4釐米
花盆在宋人花事中也別有清韻,由蔡襄著名的一件墨蹟《大研帖》,可知花盆也是用於相互饋贈的文房雅物[圖十八],雖然“花盆亦佳品”在報謝的尺牘中或有客氣的成分,但得與大研諧配,其式應當不俗,隻是這時候的花盆似以陶器或石製品為多。在花盆中蒔弄出的水石又或松梅盆景,也可作幾案小品。觀台磁州窯址發現的素胎花盆尺寸都不大,長多在二十餘釐米,高不過十幾釐米,外壁或裝飾山石芭蕉與仙鶴而成一幅庭院小景[圖十九]。花盆更古雅的名稱尚有方斛。黃公度《方斛石菖蒲》:“勺水回環含淺清,寸莖蒼翠冠崢嶸。扁舟浮玉山前過,想見江湖萬裡情。”。繹其詩意,這裡的“方斛”,也為花盆之屬。所謂“斛”,原是量器,即十鬥為斛,此便以花盆造型如鬥而假以方斛之名。花盆除用來製作盆景之外,又或育蘭與栽荷。劉克莊《詠鄰人蘭花》“兩盆去歲共移來,一置雕闌一委苔”。王炎《石盆荷葉》:“月明露冷淨娟娟,收入窗間一掬泉。不用亭亭張翠蓋,也能細細疊青錢。時因新汲分瓶杓,暗有微香散簡編。留得移根栽玉井,開花十丈藕如船。” “收入窗間一掬泉”, “暗有微香散簡編”,則一捧綠意正是盈盈於芸窗幾案。

[圖十八]素胎花檻 觀台磁州窯址出土

[圖十九] 蔡襄《大研帖》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
瓶花本來是從禮佛的香花供養而來,演變過程中伸展出室內陳設和幾案清玩的一支,且因各方面的條件適合而使得它枝繁葉茂。但本源卻依然順流而行不曾斷絕,並且禮佛之外又用於祭祀,由此發展出明清時代的所謂“五供”,即花瓶一對,燭臺一對,香爐居中,一字排開設於供案。不過宋代多見的仍是中間香爐,兩側花瓶,如遼寧省博物館藏南宋《孝經圖》中的祭祀場面[圖二十]。

[圖二十] 《孝經圖》(局部) 遼寧省博物館藏
鮮花插瓶不是中土固有的習俗,而瓶花最早是以裝飾紋樣率先出現在藝術品中,它與佛教相依在中土傳播,走了很遠的路,從魏晉直到南北朝,從西域一直到中原,到南方。瓶花雖然作為紋飾很早就是藝術形象中為人所熟悉的題材,而花瓶一詞的出現、特別是有了人們普遍認可的固定樣式,卻是很晚的事一一大約可以推定是在北宋中晚期。如果把對它的敘事分作兩個不同語彙的系統,那麼可以說一個是實物的,其中包括各種圖像;一個是文獻的,其中包括詩詞歌賦。在以實物為語彙的敘事系統中,瓶花是從魏晉南北朝而隋唐,而兩宋,直到元明清的一個始終不斷的繁榮史。而在以文獻為語彙的敘事系統中,花瓶是從晚唐五代開始進入賞愛品鑒的視野,直到兩宋才成為日常生活中幾乎不可或缺的妝點,由此而發展成為典麗精緻的生活藝術。至於兩套敘事系統的合流,則完成于宋代,並且自此以後開始沿著共同的走向,向著豐滿一途發展。